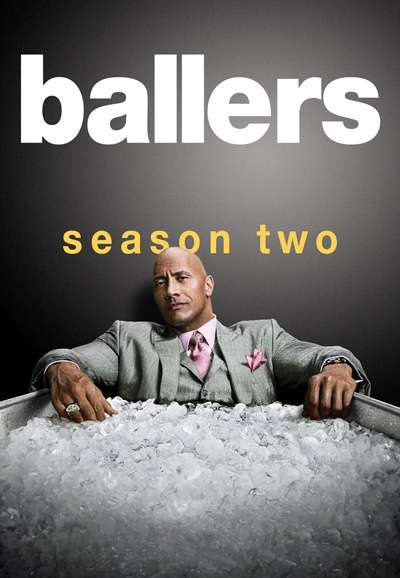《猫头鹰在黄昏飞翔》村上与川上的顶尖对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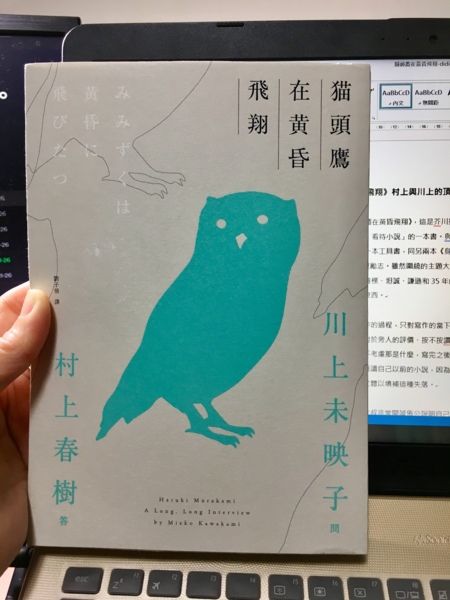
一口气读完《猫头鹰在黄昏飞翔》,这是芥川奖作家川上未映子访谈村上春树「关于如何写小说、看待小说」的一本书。与其说是访谈录,私以为对于有志写作者而言更像是一本工具书,同另两本《身为职业小说家》、《关于跑步,我说的其实是…》都很励志。虽然围绕的主题大致相同,但奇妙的是相当好看,里面有春树大叔的质朴、坦诚、谦逊和35年的写作坚持,这是我觉得他一直以来身上最可贵的东西。
村上春树很享受写作的过程,只对写作的当下感兴趣,以及如何把它贯彻到底的续航力。基本上对于旁人的评价、按不按讚、销量好不好也不在意。对于故事本身也是,事前不考虑那是什么,写完之后也不会对答案,或者思考那具有什么意义。几乎不重读自己以前的小说,因为觉得太落伍不合时宜,只能提醒自己不断写出新的文体以填补这种失落。
在这本书中,春树大叔非常开诚布公说明自己小说叙事的心法,并以长篇《刺杀骑士团长》的创作脉络举例说明。因此没读全他的所有小说,也一定要先读过《刺杀骑士团长》才能理解所谓何来。以下是阿桑个人的阅读心得笔记,里面有些内容适时解答了我在写作上的疑惑,个人觉得十分受用,彷彿看到希腊智慧女神米涅瓦的猫头鹰,飞翔在我意识形态上的有限天空。
夜已深,文长慎入,请酌量服用。
■写作对他而言并非为了认识或者治癒自己,而是借由每个虚拟人物的创造,跨界扮演另一个「我」,就像寄生在不同角色生命的演员,进入了另一个身体,经历一场有别于自己的人生,在寄生的过程中,修正并反省现在的「我」,直视内心的暗影,感受内在变化的过程。
■写作,就是把各种事物召唤过来。像灵媒一样,集中精神后,自然有各种东西主动附着在自己身上,就像磁石吸引铁片。那种磁力(专注力)能够维持多久就是胜负的关键(P.26)。
■写小说从厉害的书名开始,主角的名字也很重要。名字对了,整个轮廓(concept)就出来了。春树小说很多都是这样产出的,例如《刺杀骑士团长》、《海边的卡夫卡》、《发条鸟年代记》…都是先有书名才开始动笔,动笔之后才设定主角的职业、可能发生的事,每个要素会召唤别的要素,各自叫来各自的朋友,故事于焉展开。
■《刺杀骑士团长》是以一段事先写成的文章开头:「那年五月至第二年初,我住在狭小山谷入口附近的山上….」写好就一直放在笔电里,不为特别目的而写,后来灵光一现拿出来用。加上很喜欢上田秋成写的《春雨物语》里有一篇「二世缘」的题材,于是放进小说题材中。在地形与房子的场景描写、免色先生的造型,与叙事者「我」的关系性,则是参考《大亨小传》的人物特质。富裕的神秘邻居盖兹比,每晚眺望海边那头的绿色灯光,正如同免色先生每晚眺望山谷对面那栋屋子的灯光。这是村上春树对费兹杰罗的致敬(村上春树快60岁时翻译《大亨小传》英翻日)。
■作家的文件柜:创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文件柜(资料库建档),不断往里面塞东西,最重要的是在适当的时机,瞬间就能找到那些东西放在哪里,迅速立体组合起来。文件柜太小的人,或者忙于工作无暇塞满抽屉的人,就会渐渐文思枯竭。所以春树什么也不写的时期,便拼命把文件柜塞满,一旦开始写长篇小说就得全力应战,所以只要能用的东西统统都会抓来用,文件柜是越多越好。
■关于「人称」的思考:人称视点决定小说的格局与文体本身,也关系到叙事者自身的个性、思考模式,同时小说整体的平衡感、气氛也会跟着改变。春树早期的小说几乎用第一人称「我」来叙事,但随着年岁增长以及小说架构逐渐扩大,各种情节错综复杂,用第一人称「我」这个观点看到的世界便产生侷限,难以施展,必须改为第三人称才行,这纯粹是基于技术上的理由(P.78)。
■小说主题的构成:长篇小说这种东西,光靠一个主题绝对写不出来,需要多个主题相互纠结才能成立,便于更立体地扩展故事。如果只有一两个构成要素,故事必定会在哪撞上厚墙,变得动弹不得。所以必须先认清自己脑中有多个重点,否则不能动笔写长篇(P.79)。
■场所舞台的建立:《刺杀骑士团长》的画室,先有画家「我」,各种人开始出入「我」的画室,然后每个登场人物各有状况,把那状况带入故事中,如此一来故事就能不断前进。如果一开始就先决定什么样的人出现发生什么事,就不会产生这种自发性的动向(P.80)。
■小说构成的要素:包括故事设定、登场人物或场景描写等,但最后还是会归结到文体。文体如果变了,变得崭新或者进化,即便一再重复写同样的东西,还是会成为新的故事。只要文体不断改变,作家就无所畏惧,带着血肉持续更动,一切就会截然不同(P.182波赫士的举例)。
■书写地下二楼的故事:小说家说故事,是让自己下降到意识的底层,走入心灵的黑暗底部。所谓日本的私小说,大概就是「地下一楼的烦恼室」,如果写作只是为了书写并疗癒自己,把那私密部分公开给外人阅读参观,似乎是非常危险的行为。因为小说家要认识自我,并非要写自己,而是在于淬鍊文章的这个行为本身。
■想写的念头满溢时,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写出来,一直往前写,把眼前出现的东西一个不漏地捕捉下来,每天四千字。完全没灵感时就描写场景,无论如何都要写四千字,这是规定。初稿也许粗糙,或是出现情节矛盾之处,但先不用管它,之后再回头调整就好(P.45)。
■推理小说家瑞蒙.钱德勒是「比喻」的天才。所谓的比喻,是用来突显意义性的落差,小说需要这种惊喜。
■春树大叔小说里的性爱,多半是某种仪式性、精神性的入口。大叔也提到,拥有某种程度精确度的写实主义文体,加上故事的「离奇性」,可以制造出非常有趣的效果。性爱场景也很难写,一边觉得受不了、难为情,一边努力写了很多性爱场面,结果甚至被批评「村上是个情色作家」(笑)。村上说到现在都还觉得很难为情。
■主角「我」的中立性格,是用来参差对照其他的人物角色。因为中立,才会不断被捲入故事核心,去各种场所经历奇特的、不可思议的体验。例如《白鲸记》和《大亨小传》,主角是中立的,所以周遭的怪人们的个性也会显得特别写实生动(P.142)。
■推动故事的引水人:《刺杀骑士团长》表面上以画家「我」为叙事者,但免色先生又似乎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角色。春树在书中也坦言,这个谜团般、来历不明的人物,对他而言同样来历不明,自己也无法清楚说明免色到底是甚么样的人。甚至书名的副标题Idea(意念)、Metaphor(隐喻)也跟柏拉图主义无关,纯粹只是喜欢这个单字的发音,以及字义本身的丰富性,再加上用魂魄、灵魂、spirit…的说法都不够贴切,只有idea特别吻合「骑士团长」。至于书中那位「长脸的」,只有Metaphor这个字眼最顺眼,于是就这么顺着走,村上只是写出它,靠它自己走(对于村上的坦率,阿桑有点吃惊,原来根本没有所谓的定义)(P.153)
■形塑人物的立体性、增添血肉的方法,是透过一些小动作、三言两语这些细节的描写,让人产生印象。
■小说家的社会性:对60年代的学运感到幻灭,耗费大量言词却轻易瓦解怀有强烈愤怒,口号式的语言成了表面文章,一种语言的空转和滥觞,世界也没因此而改变。日本历经泡沫经济、神户大地震、311大地震、福岛核电厂事故…身为社会一份子怀有强烈的危机感,觉得必须做点甚么。因此如何思索遣词用字,找到「写小说」与「文以载道」之间的界线,分寸的拿捏相当重要(P.60)。
走笔至此,想起前阵子读是枝裕和《我在拍电影时思考的事》,也提到类似的观点。当年主导学运的婴儿潮世代,现在却成天打高尔夫球,让崇高的改革热情沦为青春岁月的一页篇章,自己心中那种青涩的理想主义无从安置,偏偏又找不到新的价值感和消弭不安的方法,只能成天郁闷不欢。
■不能养赘肉,要过规律的生活,而且要沉潜到内心深处,又能维持体力足以从底层回来,这是身为职业小说家很重要的事。
■不让读者睡着的唯二窍门:「戏剧性的对话节奏」,「具象生动的比喻」。春树引用钱德勒的比喻:「对我来说失眠的夜晚就和胖邮差一样罕有」,这句话绝对比「对我来说失眠很少有」更让人印象深刻。
■奥森.威尔斯的电影《大国民》中,从义大利请来的声乐教师,对立志当歌手的凯恩之妻失去耐心,说道:「世上分为两种人,会唱歌的,和不会唱的(Some people can sing, some can’t.)」这是很有名的台词,也许对于写作也是,有些事确实需要天赋,但后天的努力可以慢慢累积。没有人是天生的作家,大家都是一边领稿费一边慢慢进步的。
■作家如果不能用眼睛听见声响就不行。写文章,重读,不是出声朗读,是用眼睛去感受声响,这非常重要。「所以我总是说从音乐学习文章的写法,用眼睛看,去感受那个声响,订正声响,让它发出更美妙的声音。我很重视这个。逗号和句点不也是节奏吗?那个也很重要。」
■村上春树曾荣获安徒生文学奖,在致词演说中,引用了安徒生写的《影子》这篇小说,对小说家而言,重要的是影子,必须尽可能诚实正确地书写那个影子。不逃避,也不须用逻辑去分析,只要当成自己的一部份接受,描写融入内在的它,分享那个过程的经历对于小说家而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影响。
■村上也喜欢写音乐评论的文章,但不是去评论,而是写自己听音乐的喜悦。如何用文章表达音乐非常困难,但是可以训练自己写文章。比如说舒伯特的长调钢琴奏鸣曲作品D850该如何置换成文章,那就好比写炸牡蛎一样困难。思考如何「用文章」创造出那种「炸牡蛎」的实感,写出身体的物理性反应,让读者只看字面就湧现好想吃炸牡蛎,那种非读不可的渴望。
转载请注明源自 每日美剧 www.meirimeiju.com